
凌晨四点的西安,天刚蒙蒙亮,闫芳军的身影已出现在案板前。掌心按压在发酵好的面团上,凉丝丝的触感漫过指尖,随着臂膀发力,面团在案板上发出沉闷而规律的“咚咚”声,像是在与这座古城的晨韵共鸣。这位被称作“西北面王”的汉子,用半辈子的时光,将一捧普通的面粉,揉成了承载匠心与传承的故事。
一、五十块钱与一个面团的初心
闫芳军的故事,始于甘肃天水汪川乡下的一间小面馆。16岁那年,家境贫寒的他揣着母亲给的50块钱,跟着同乡踏上了学做面的路。“学门手艺饿不死,做面要实在,待人要真诚。”母亲的叮嘱,成了他刻在心里的准则。
初学时的日子,是磨人的。师傅不让他碰面团,每天的工作是凌晨3点起来烧火,灶台比人还高,烧火棍抡得胳膊生疼;中午蹲在灶台边洗碗,冬天的冰水冻得手上全是裂口;晚上则跪在案板上扫面粉,稍有不慎就会挨骂。“那时候最大的愿望,就是能亲手揉一次面。”闫芳军至今记得第一次偷偷摸到面团的感觉:“凉丝丝、沉甸甸的,像握着一块有生命的东西,你用劲它就较劲,你顺着它,它就服帖。”
为了学到真本事,他比谁都拼。别人练拉面累了就休息,他回宿舍把被子卷起来当“面团”,闭着眼练手法,直到胳膊抬不起来;师傅说“醒面要见功夫”,他就整夜守在面缸旁,每隔半小时记录一次温度和面团变化,三个月写满了两本笔记;为掌握刀削面的角度,他用土豆当练习材料,一天削坏三副刀,手指划得全是口子,包着纱布继续练。手掌上厚厚的茧子,是那段日子最真实的印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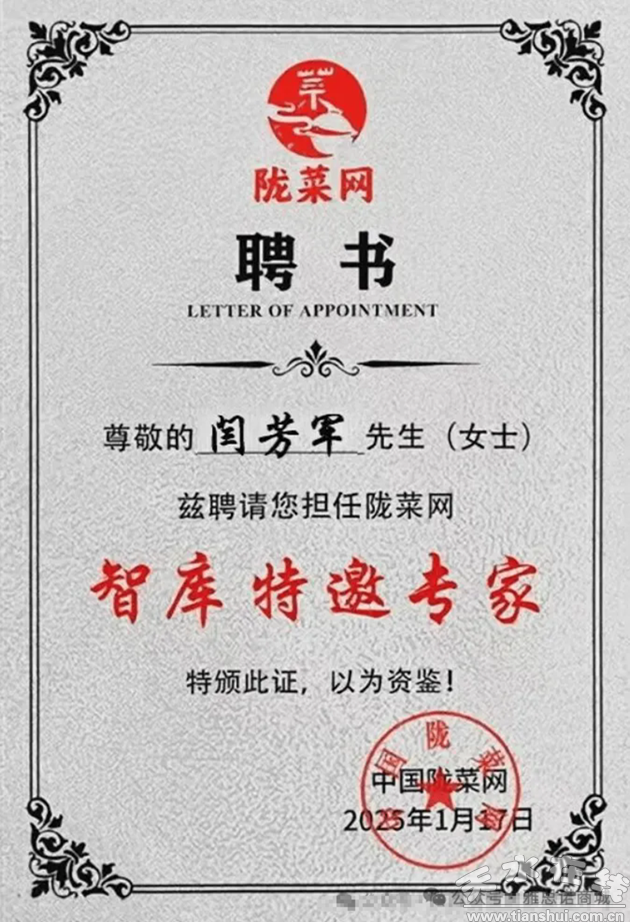
二、面团上的绝活:从灶台到舞台
多年的苦练,让闫芳军的手艺日益精湛,而“面团吹气球”这一绝活,更是让他名声大噪。这看似魔术的技艺,实则是对揉面功夫的极致考验——将发酵好的面团揉成球状,用嘴吹气使其膨胀如气球,再在薄如纸的球壁上切菜、写字,既需面团有足够韧性,又要拿捏好力度。
“刚开始练的时候,吹得脸通红也吹不起来,要么一使劲就破了,要么形状歪歪扭扭。”闫芳军笑着说,发酵时间、水温、揉面力度,差一点都不行。经过半年多的琢磨,他终于掌握了其中的诀窍。2024年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,他当众用气球面团切出“长安”二字,切痕整齐如刀刻,气球却完好无损,全球观众透过屏幕,看到了西北面食“刚柔并济”的神奇。
“好的面团能拉长到原长的8倍,回弹率极高,这就是西北面的‘骨气’。”闫芳军拿起一块面团轻轻一拉,面条瞬间延展又迅速回弹。在他看来,西北面食的特别之处,不仅在于这股“骨气”,更在于“一料一炒,一面一味”里藏着的水土与人情——臊子面的酸香、油泼面的火辣、浆水面的清爽,都是西北大地的馈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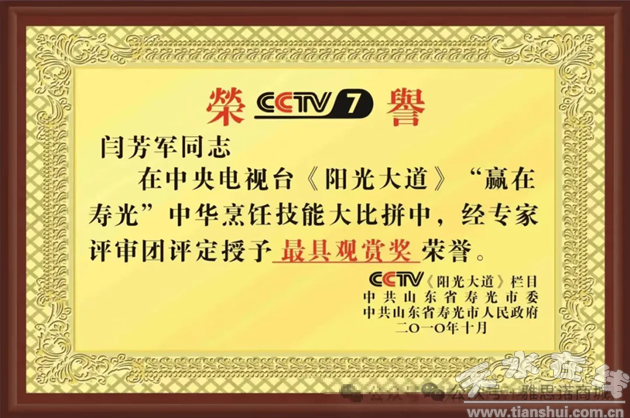
三、传承的责任:让更多人爱上西北面
“一个人强不算强,一群人强才是真的强。”如今的闫芳军,肩上多了份传承的责任。作为国家餐饮业一级裁判员,他参与制定《西北面食技艺评定标准》,把“盐少许”“面适量”这些“凭感觉”的老经验,转化为醒面温度25到28摄氏度、揉面时长不少于15分钟等可量化的指标,让新人学起来有章可循。
每年,他还以陕西省饭店协会面点小吃专业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,组织“西北面食交流会”,让各地师傅聚在一起切磋技艺,你教我拉面手法,我传你调汤秘方。他创办的“西北面王美食工作室”免费培训了多名学员,从揉面的“三光”(盆光、面光、手光)技巧到醒面的温度控制,毫无保留。
在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校区,闫芳军不只是食堂师傅,更是学生们的“面食文化老师”。有学生好奇他做的面条为何特别筋道,他会拉着学生看面团的弹性测试;他带学生去面粉厂参观,讲解“从麦粒到面粉”的过程,告诉他们:“每一粒麦子都不容易,做面的人得懂感恩。”有学生毕业后开了面馆,寄来自己做的面,说“客人都说好”,那一刻,闫芳军比自己拿奖还高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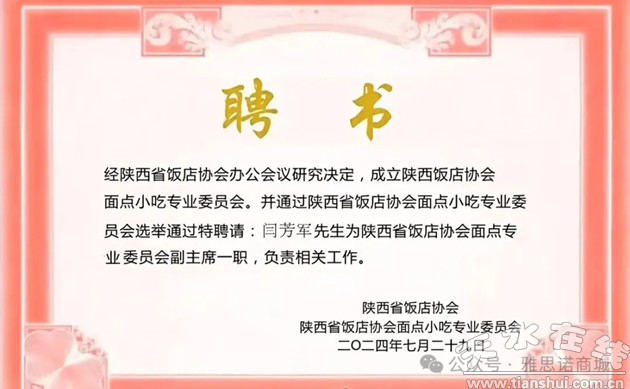
四、面粉里的坚守:麦香与匠心
从街头学徒到“西北面王”,从灶台到舞台,闫芳军的半辈子都与面粉为伴。他说:“我没啥大本事,就想让更多人知道,咱西北的面,不只是能吃饱,更有说头、有看头、有传头。”
如今,他仍保持着每天凌晨4点起床揉面的习惯,案板上的面粉簌簌落下,像在书写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。故事里,有山沟里的麦香,有灶台上的匠心,更有一个西北汉子对土地最质朴的爱。而那团在他掌心旋转、舒展的面团,正孕育着西北面食更长久的生命力。(刘建斌)
